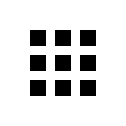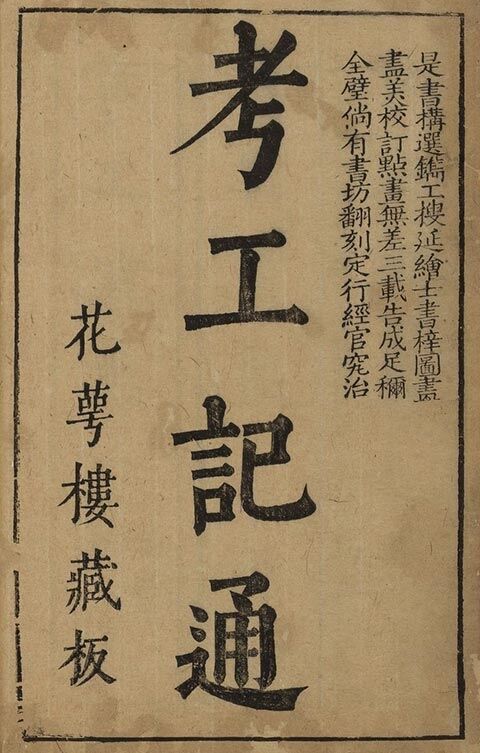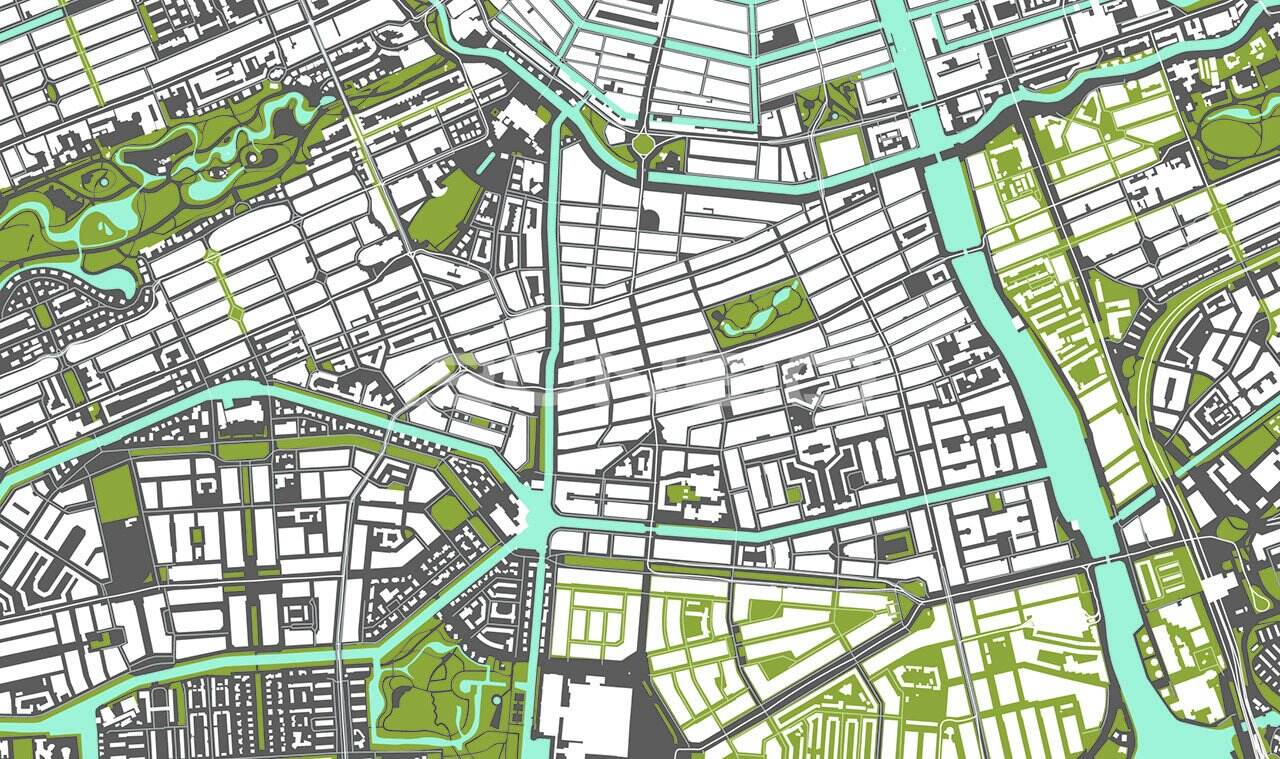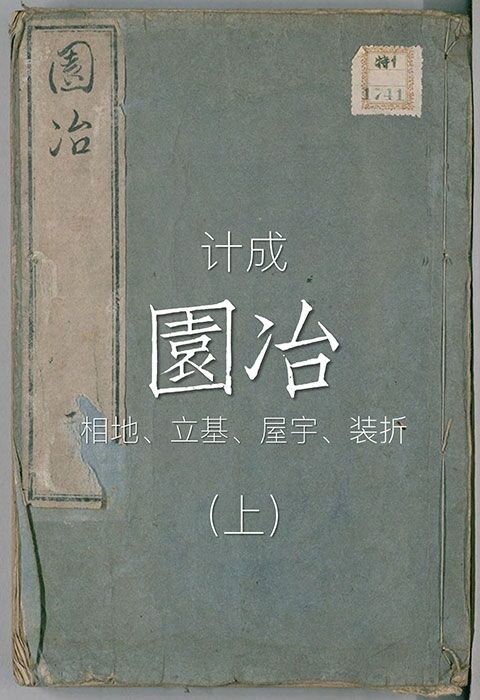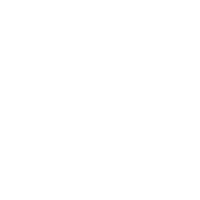郑时龄:丑陋建筑背后的文化生态
中国建筑学会 郑时龄 2016-09-16 19:30
某市“东方之门”还未戴上“世界第一门”的桂冠,却先因形似“秋裤”而遭网民集体“吐槽”;自比鸟巢,却落鸡窝之讽的某市美术馆,近日也因入选“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候选名单而“名噪一时”。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出现造型怪异、庸俗不堪的“著名”建筑,粗暴考验着人们的视觉。这些建筑大多在设计、建造之初,不为公众所知,即使公众知情并反对,也难以阻挡其“丑陋”进程。假如,属于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远离了这座城市所向往的精神气质,游离于生活在城市时空中的公众的文化心理,那无疑是城市公共建筑在美学和文化上的败笔。
建筑的丑陋,不仅仅是一种表象。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教授,深度剖析了丑陋建筑背后的文化生态,倡导一种可以优雅传递城市精神的建筑与建筑文化。

郑时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
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异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气比造价重要,形式比内容重要
Q:最近有网站开展第三届“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关注和参与投票的人众多。类似的评选还有不少,这些评选虽然不一定权威、客观,但却是公众情绪的一种表达,因为人们对丑陋建筑忍无可忍。
郑时龄:说实话,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也有这类建筑,虽不至于列入丑陋建筑排行榜,但它们和环境显然是不协调的。比如徐家汇天主堂旁边的一座大楼,它的屋顶与建筑的主体关系就很不协调,而且,周边是教堂、修道院、藏书楼等教会建筑,突然冒出一个中国古典的大屋顶,破坏了整体环境。再比如浦东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代表了面向未来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一幢170米高的金融大厦采用了仿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基座就像古希腊的神庙,显得很突兀。身处城市空间之中,各个建筑间要彼此能够对话,像大合唱一样,各个声部都要和谐
Q:这个“大合唱”里,是否时不时会冒出不和谐的音符?
郑时龄:是的。不和谐的音符,有很多是照搬国外的山寨建筑,美国的国会大厦、法国的凯旋门、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等建筑,都可以在国内各大城市找到粗陋的仿制品。上海一所大学的新校区,行政楼是法国式的,学生活动中心“拼贴”了意大利两幢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整个校园的建筑风格似乎是一个脱离了现实文化环境的“洋杂烩”。
也有一些自称使用中国元素的建筑,却更像一种异化的民族印象。北京一家酒店,整幢楼就是“福禄寿”三星造型,把民间对金钱、权势的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沈阳的一座大厦,显示了设计者对“孔方兄”的尊崇和热爱。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建筑只是一些简陋的相似性的联想,甚至连联想都没有。
Q:还有一类建筑,就是一味追求高大宏伟。
郑时龄:这是当下的一种风气,盲目贪大,一味攀高。全世界20幢最高建筑,其中11幢在亚洲,而11幢中就有9幢在中国。据说,到2016年,全国不少二三线城市都将出现超高层建筑,某地甚至还有两个月建成一幢比迪拜哈利法塔还高10米的大楼的计划。这些过分高大的建筑,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显得突兀而缺乏美感,但它们却很可能满足了某些人对政绩和荣耀的追求,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异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气比造价重要,形式比内容重要。事实上,足球场那么大的浮雕和摩天大楼那么高的门,也仅仅是大和高的丑陋而已,公众不会喜欢,这样的建筑注定是悲哀的。
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学试验,不是搭积木,不能为一个结果而做无数次的试错性试验
Q:去年,财政部和住建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要求避免建筑外形片面追求“新、奇、特”,但为什么丑陋建筑还是不断在出现?
郑时龄:通知、条例往往只能规定数据,无法规定艺术创作的水准。更关键的是,有些公共建筑并没有代表公众审美,往往是某些利益集团、甚至个人的审美。我们知道,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是目前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而城市建设相对经济发展来说往往见效更快,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短平快”的建设节奏,加上某些领导“特殊”的审美需求,难免出现一批“非正常建筑”——它们开工快,建设快,忽略公共的美丑标准,成为权力在建筑领域的“图腾”。要知道,审美虽然带有主观性,但在任何一个时代,美丑都有相对明确的公共标准,建筑也是这样。尤其是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必须在公共审美体系的框架内进行创作。更深层次地说,如果将丑陋作为主动策略,让相关企业获得额外的品牌效应,这更是对文化和审美的漠视。
Q:当这样的没有代表公众审美、拒绝与周围环境对话的建筑,以强势的姿态在城市中出现时,公众的心理可能产生抗拒。
郑时龄:抗拒的产生,根源在于现在我们的一些建筑话语其实已被代表权力或资本的威势话语所取代。举个例子,有个房地产开发商在招标的时候,根本还没有看到美国公司的设计方案,他就坚决地说,一定要采用美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所有竞标方案中,美国的设计是最糟糕的。
Q:这恰恰又证实了今天中国建筑领域的一个微妙心态与现实,很多项目青睐、采用外国设计师的方案,乃至出现了一种较为极端的说法——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对此您如何看待?
郑时龄:这话虽然极端,却也道出了某种倾向。比如,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设计与文脉、环境很少有呼应关系,因此很少能变成现实,而在中国她却大展身手。上海曾有一个历史建筑保护项目请她做设计,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毕竟,即使是国际上最优秀的建筑师,他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我们不能只看国籍和名气。
其实,我对试验本身并不反对。建筑需要试验,就根本而言,建筑史上的每次创造都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都是一种试验,建筑师永远会面对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新环境等。但建筑试验分为物质试验和思想试验,思想试验应当先于物质试验,在以实际行动运行一种程序以前,必须在头脑中先具有这种“程序”。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学试验,不是搭积木,不能为一个结果而做无数次的试错性试验。
说到底,试验场的问题,不在外国建筑师,而在我们自己的选择。现在不少大规模建设项目,邀请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他们对我们的城市和文脉缺乏理解,由此导致了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历史城市的怪象。设计者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很可能伤害属于城市自身的文化认同。
建筑师自身人文素养的缺失,制造了建筑“怪兽”,也制造了建筑的轻率
Q:您如何看待建筑师自身人文素养不足与丑陋建筑的出现之间的关系?
郑时龄:这个问题我可以借用别人的话来回答。1985年,美国弗吉尼亚建筑学院召开了一场关于高层建筑的讨论会,众多国际建筑明星参与了讨论。会议上,奥地利建筑师罗伯·克里尔说:“身为一个艺术家或建筑师,你们是唯一可以下判断的人,也是负全责的人。在替业主设计了很多高层建筑后,你们却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替别人做事。我想把你们丢到炼狱里去,因为你们很清楚自己在做错的事!你们不只在建造建筑巨兽,也制造了现代建筑的轻率。”现在有些建筑师就是在制造建筑“巨兽”和“怪兽”。
Q:对自己设计的建筑来说,建筑师永远不能逃避的是社会责任。
郑时龄:如果建筑师对自己的作品所要落实的这片地区、这座城市,大而言之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缺乏应有的理解,甚至缺乏去理解这些元素的基本的真诚,缺乏敬畏心和责任心,就很容易简单地以西方的某些概念和话语来抽象地看待建筑美的标准,发展到极致,就是美与丑的颠倒。
责任之外,现在有些建筑师缺乏审美能力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有一次看到电视上采访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他说:“我用东方的哲学来理解西方的音乐。”但是我们建筑界现在就缺少这种理解,过去像梁思成这样的大家学贯中西,现在我们中也不通,西就更不用说了。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建筑师是乐队的指挥,建筑的学问是广泛的,应该熟悉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也要学习历史,深谙哲学,理解音乐,对天文、医学、法律等也并非茫然无知。而现在人才培养上的实用主义,却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高考制度,中学阶段忽视科学教育和审美教育,使得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缺乏人文素养;大学的教育又倾向于工具理性,忽视人文理性。我曾对自己教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做了一个有关课程比例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小学时期,语文课与外语课的课时平均比例为1.33:1,到高中阶段,这个比例就倒过来了,大学阶段则只学外语,不学语文,外语课时远超专业课。虽然语文课不一定就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全部时间,但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今天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某种不足。
Q:这和整个社会的氛围也密切相关。
郑时龄:我们现在经济的步子走得很快,但骨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好好面对。据统计,西班牙平均每1800个人中就有一个建筑师,美国每3000人里有一个建筑师,而中国每3万人才有一个建筑师。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调侃中国建筑师说:“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他们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数量5倍于美国建筑师的建筑,只收取了1/10的设计费。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我认为,要创造当代中国的优秀建筑,必须抛弃求多求快的作风,避免非理性的规划。伦敦、巴黎、纽约、巴塞罗那等城市并不是因为大型硬件建设、大规模开发而享有盛誉,而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特色鲜明的文化和不断推进新观念的氛围。
现在有很多建筑师喜欢像上帝那样,从天上往下看。而真正的建筑大师始终关注的是建筑的内在,“上帝在细部之中”
Q:人们用“坍塌的柴火”、“垃圾杂物堆”等词语来形容某市美术馆。面对质疑,建筑师以“创新”作为回应,“我的灵感来源于儿童的游戏棒,它的造型正是将游戏棒自然散落后的状态进行固化,以形成一种自然状态下鸟巢形状的自然美感。”很明显,“创新”已成了很多丑陋建筑的设计者的一个“挡箭牌”。
郑时龄:不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创新。创新不是表面的东西,而在于发现并解决问题,必须适应现实,在尊重环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新。创新在变成一种口号以后,很容易走向标新立异,仅把“新”作为目标,而忽略了“创”。
Q:所以,现在一些纯粹追求外形新奇、并将其定位为“现代性”的建筑,其实是对创新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郑时龄:是的。现代性是当代建筑的核心问题,决定着中国当代建筑的理性现实和理想未来,决定着中国建筑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建筑领域既需要引进并学习西方的建筑文化理论,也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的建筑文化理论,要处理好建筑现代化与传统建筑文化、中国建筑文化与世界建筑文化的关系。
Q:梳理了种种建筑的丑与丑的原因之后,回到采访的原点,您认为怎样的建筑才是美的?
郑时龄:西班牙建筑师莫奈欧在大西洋畔的圣塞巴斯蒂安海边设计了一座库尔萨尔文化中心,建筑与环境融合得很完美,就像是从沙滩上生长出来的。挪威奥斯陆歌剧院,仿佛是挪威冬天白雪皑皑的山脉。这些经典案例都在告诉我们,美的建筑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天外来客”。
更重要的是,再美的建筑首先要安全、实用。我国有明确的建筑规范:安全、实用、经济、美观,首要是安全和实用,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但现在很多建筑设计一味追求“新、奇、特”,安全系数下降,造价飙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可以做一些漂亮的建筑,但要有限度,跟风山寨“鸟巢”、国家大剧院这样的标志性建筑,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外,不过是落得东施效颦的下场。
建筑有自身的规律,好的形式不一定是好的建筑。现在有很多建筑师喜欢像上帝那样,从天上往下看。而真正的建筑大师始终关注的是建筑的内在,“上帝在细部之中”。
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的城市构成的。一旦城市不再是艺术和秩序的象征物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
Q: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建筑的美丑,本身就有一定意义,代表了公众意见的介入。
郑时龄:当公众逐渐培养起对公共建筑的审美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建设和舆论监督后,就能形成合力抵制丑陋建筑带来的视觉公害。像“酒瓶楼”、“大裤衩”、“秋裤”等词汇,正是建筑“形象”叠加“评价”的特殊符号语汇,证明建筑具有人文和美学的双重属性。当然,关于建筑审美的分歧会一直存在,恰恰是这种分歧,会构成推动与完善建筑生产的力量。丑陋建筑是一种视觉公害,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在大众传播上做更多的努力,让建筑话题成为媒体的重要话题,成为美术馆、博物馆的活动主题,以推动全社会对美好建筑的集体追求。
Q:丘吉尔曾经说过:“人塑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城市也同样如此。我们塑造城市的过程,实际也是在塑造我们自己和未来。
郑时龄:建筑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去别的国家旅游,必定会去看城市,拍照时也往往把那里的标志性建筑作为背景。建筑集中表现了城市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而城市又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的城市构成的。一旦城市不再是艺术和秩序的象征物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
Q:好的建筑,对城市意味着什么?
郑时龄: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曾是西班牙北部重要的钢铁与航运城市,1975年以后,伴随着制造业危机,这座城市进入衰落期。城市管理者试图调整结构,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通讯业和旅游产业,但怎样吸引游客成了最大的难题。1997年,他们造了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就是这幢建筑每年吸引了200万游客,为这座城市每年带来0.7%的GDP收入。
Q:可以说,建筑与城市是互为表达的。
郑时龄:建筑和城市空间是意识形态的物化。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城市凝聚了人的创造力和智慧,同人一样,会思想,会进化,会与自然对话。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形、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文化的具体符号。优秀的建筑需要全民的扶植和培育,需要全民善待我们所身处的经历发展演变而来的城市,尊重历史,尊重文化。
来源:中国建筑学会 2013-07-09
热门话题
hot topics